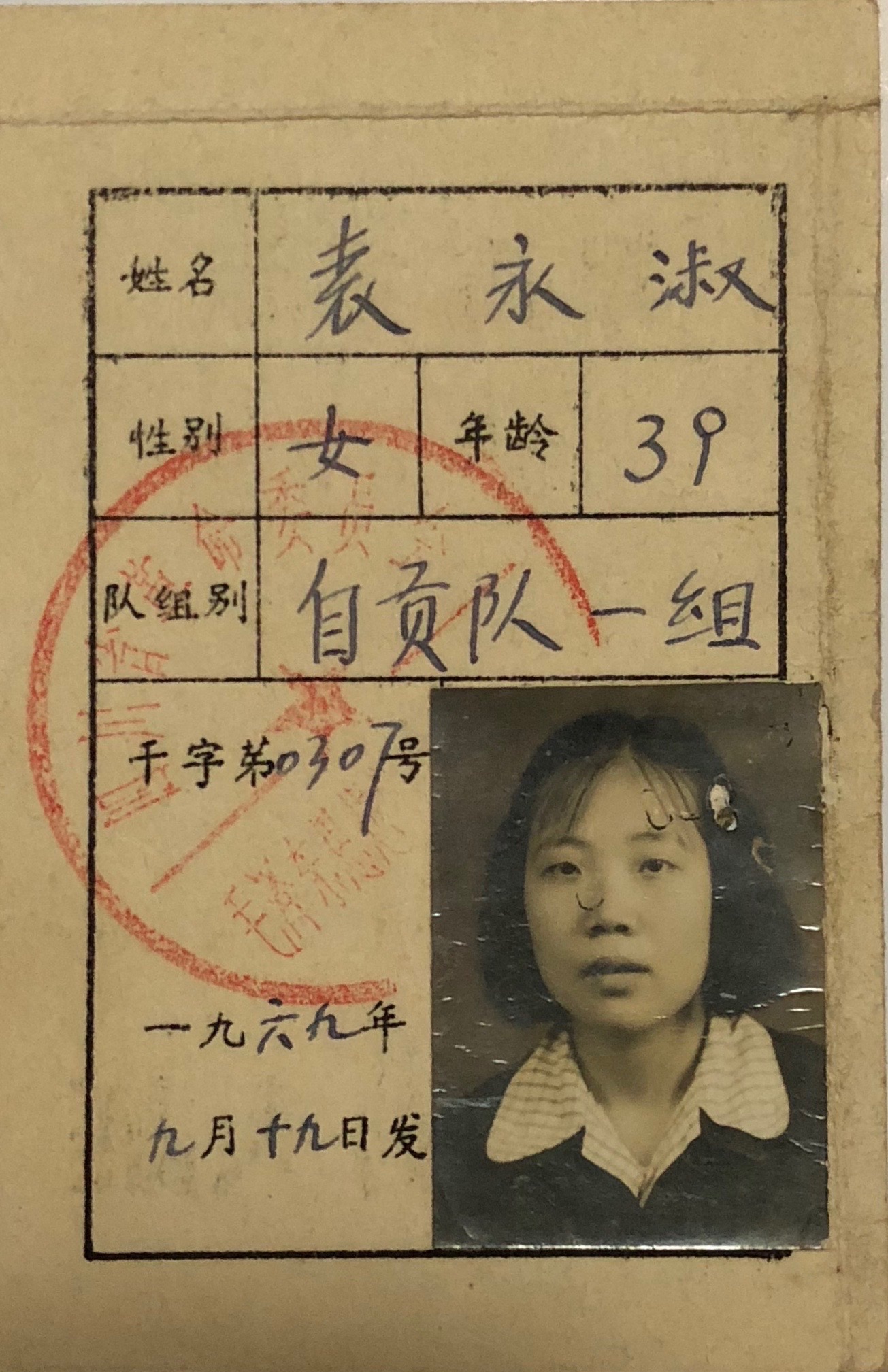2022-03-18, 周五,20°C
今晚和哥哥一起聊爸爸妈妈聊从前,哥哥提到罗湾的家里有一个黑漆木凳,他说:“我们三五岁在罗湾时,那木凳是我俩的饭桌,我们在小桌上吃饭时常为抢菜打架。”
聊完天,那黑漆木凳很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我们家的黑漆木凳有一尺宽两尺长一尺半高,叶姨很喜欢讲这个木凳历险的故事,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这个木凳的家史。虽然我在网上没有搜到记忆中类似的木凳,我想那黑漆木凳在哥哥的记忆里还是我熟悉的样子。手足情可能是人生最长久的亲情,爸爸妈妈过世了,我和哥哥的手足情已经是我今生拥有的最长久的亲情了。感恩这份亲情,为回忆从前增添无穷乐趣也带来动力。
1968年前,我们住在市委机关的北苑,我们的家具都是公家的。当我们要从北苑搬到罗湾时才知道家里连一张吃饭的桌子都没有。家公知道此事后就匆匆地从袜子石家里拿来一个木凳,经塘坎上的北苑大门送到我们家。我们是从北苑在五十梯附近的关外大门搬出来,因为这道门离罗湾更近。搬家时北苑的大门口都有造反派把守着,所有家具都要经过造反派目测确定不是公家财产后才能搬出北苑。家公从塘坎上的大门带进北苑的木凳却带不出关外的大门,因为守门的造反派一口咬定这木凳是公家财产。叶姨每每讲到这里都会义愤填膺地说:“从前觉得很好很熟悉的人,一当造反派就变了,还装着不认识我一样。我大吵了一通才把这个木凳搬出北苑。你们现在才有一张吃饭的桌子。”
妈妈说过:“那黑漆木凳我小时候就知道是用榫卯(没有一根钉子)装起来的,算一个古董了。”
我们刚搬到罗湾还没有厨房,吃饭睡觉都在一个房间;妈妈接连去长沙坝水库劳动和去成都上学习班,家里就叶姨带着哥哥和我。我还记得哥哥和我坐在木凳两头吃饭抢菜打架的故事。叶姨把菜放在木凳中间,为抢菜哥哥会把木凳往他那边拉。我力气没他大,拉木凳总拉不过他,木凳离我远我够不到木凳上的菜就会叫唤。叶姨就把菜事先分给我们,以免我们拉凳子抢菜打架。叶姨买鲢鱼切成拳头大小做坨坨鱼时,我们会连着几天吃美味的坨坨鱼,我记得我会慢慢地吃我的那份坨坨鱼眼气哥哥,因为哥哥会很快把他的那份鱼吃光。
叶姨过世后我问过妈妈:“小时候听叶姨讲故事,我觉得她在北苑认识很多人,怎么会呢?”妈妈一听就笑了,然后告诉我:“你叶姨在北苑小有名气。”我又问:“为什么?”妈妈想了想说:“你叶姨和赖姨是好朋友,赖姨在李唐基家里带小孩,李唐基是市委书记。有句老话:‘宰相门前七品官’。”这让我想起了喜剧《七品芝麻官》。
哥哥读了这个故事后,我们一起分享了我们的搬家历史,算是这根黑漆木凳引出来的一段家史。
哥哥还说:“记得我们家有一个乌木大衣柜也是黑色的,好像这个柜子是在新街口的一个日杂公司门市部买的二手家俱,大概花了不到一百元,现在也算我们家的一件古董了。1998年北漂后,我们在北京又搬了七八次家,等真正稳定下来是2003爸爸妈妈搬入了岳各庄民岳家园后。现在记不得大概是哪年,大概是2006年前后爸爸妈妈回自贡清理老家的东西,把不少书和妹妹的书信和这个乌木柜打包通过铁路托运来北京,这时已经有了搬家公司了。”
哥哥的几位中学好朋友:王全,雷国钢,周永强,任加齐,我都很熟悉,其中有两位是兵哥哥。不过有故事的只有两位。
王全的家在东兴寺的盐分巷里头,他是盐务局的子弟。他有一个哥哥,他爸爸非常高,他妈妈很娇俏。记得哥哥说过:“王全的妈妈青光眼痛起来时,他爸爸抱起他妈妈就去医院。”东兴寺的公交车极少,我那时就想王全的爸爸抱着他妈妈大概是走路去医院的,所以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雷国钢的妹妹雷国强和我是东兴寺小学的同班同学好朋友,我记得雷国钢在东兴寺小学是出名的调皮大王之一,他爸爸是电业局的司机,他们家在毛家坝附近。他上中学后成了我哥哥的好朋友,高中毕业后上军校做了军官。哥哥和哥哥,妹妹和妹妹都是好朋友的不多,所以我当过红娘为雷国钢牵线,但是没成功。2008年我回四川时,雷国强特意赶来和我见了一面,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几乎没变。她告诉我小云的电话号码,我才联系上了小云和Karan并延续起我们从自贡东兴寺小学到美国硅谷的发小闺蜜情。她还给我解释了为什么我给她哥哥牵的线没有成功的原因。
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兴寺的公交车极少极不频繁,只有两个相距百多米的汽车站。郊外公交车站在盐务局对面火车铁桥下面,是从毛家坝隆矿开过来;另一个市内公交车站在东兴寺茶馆对面,是从牛奶场一对山开过来在蔬菜店转了个大弯的市内公交车。我在自贡一中上初中那三年,有时计划坐公交车上学却经常眼睁睁地错过公交车,因为那个年代的公交司机很毛糙,不会等着让乘客跑到上车后才开走。我现在还常梦到我在东兴寺焦虑地盘算着是在东兴寺茶馆对面等市内公交车还是去盐务局门口等郊外公交车,因为错过公交车的痛太深刻了。
小插曲